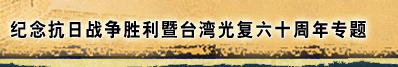13年間,蘇智良行萬里路:從東瀛到上海,從白山黑水到黃土高原,從冰封北國到炎炎海南,跨過長江黃河,遠赴云貴高原,采集證人證言。
13年間,蘇智良讀萬卷書,遍閱相關日偽檔案,日本人在華文獻和書籍、日軍老兵回憶、戰時報刊資料……
13年間,蘇智良自掏30萬元,用以調查取證、補貼老人生活。
“一切為了真相”:還慰安婦歷史一個真相,告慰20萬曾遭日本法西斯凌辱冤魂的在天之靈。
一張舊照片開啟一段被抹去的歷史
1991年,蘇智良作為訪問學者前往東京大學。“東京大學離著名的舊書街神保町不算很遠,一天在神保町的舊書店里,我發現了一張照片:黑白照片上有兩排日本木屋,中間是碎磚鋪就的路,一個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,正準備進入慰安婦的房間去作樂。旁邊的文字說明是‘上海楊家宅慰安所’,1938年1月建立。”當時的中國學者對慰安婦知之甚少,國內研究尚屬空白。
“上海”“慰安所”這兩個詞揪住了蘇智良的神經,這個楊家宅慰安所在上海的哪里?日軍為什么要設立這個慰安所?是誰經營的?里面的慰安婦來自哪里?這個慰安所后來怎樣了?房子還在嗎?還有沒有知情者?“這些問題始終縈繞在我心頭。”
1993年6月,蘇智良結束了在日本兩年的留學生活,和夫人乘船從橫濱回國。“在日本所得的慰安所線索僅僅兩條。回到上海,我迫不及待地開始實地調查。”“當初做研究時,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有今天的結果。”蘇智良拿出自己剛剛出版的《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》:“這本書是今年4月截稿的,里邊收錄了我13年間在上海尋找到的149家慰安所。但書出版僅兩個月,又有市民打來電話,提供了4個慰安所的線索。”
13年的研究,蘇智良在上海找到了日軍海外的第一家,也是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家慰安所:“大一沙龍”;也找到了舊照片上的楊家宅慰安所……從2到149,到153,數字還在增加。“我震驚了!真沒想到有那么多。”
采集三百慰安婦血淚證言
妻子陳麗菲,原本是學古代史的, 1997年去陜西,為了方便采訪,蘇智良第一次帶上了妻子, “我是男人,總有不方便之處。”這一次山西之旅,他們共走訪了14位原日軍慰安婦。
“妻子很容易落淚,在采訪過程中有好多次和老人抱頭痛哭,采訪沒法繼續。”回上海之后,陳麗菲毅然辭掉了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工作,專心一意陪丈夫開展調查工作。
“研究慰安婦歷史是痛苦的,心理壓力實在太大。”蘇智良和妻子講起了幾件難以忘卻的故事。2000年,蘇智良帶南京的一位楊大娘去大阪講演。老人在前臺的一塊白布后講演。老人緩緩開始講道:“我八歲在南京遭日本兵輪奸,后成慰安婦,到現在每天都要用尿布。”聽到這里,“我眼淚頓瀉,無法抑制。”
2000年,蘇智良想帶云南的李連春老人去東京作證,可是地方政府卻在成行前夕橫加阻撓,有的干部甚至說:“這么丟臉的事做過了,難道還要去宣揚?!”
為此蘇智良、陳麗菲親赴云南,住在老人家里開導她,老人淚流滿面地說道:“我的身體是干凈的,日本鬼子才是臟的。”“老人說話時的語氣、眼神至今刻在我大腦里。”陳麗菲無法忘記。
這么多年來,夫婦倆訪問的慰安婦超過三百人。“實證調查對歷史學很重要。我做的歷史關乎普通人的苦難和掙扎。”撫著案頭的文案,蘇智良說道:“她們的證言都在這里,鐵一樣的證據。”
“慈善家”蘇智良
自從第一次見到原日軍慰安婦,蘇智良就明白了,他所做的已經超越了歷史學的邊界,一個學者的邊界。
就在接受采訪之前,蘇智良剛剛讓自己的一個博士給山西14位原日軍慰安婦送去了15600元生活補貼。同樣的事情,他每年都要悉心安排,“據我的統計,全國至今尚健在的日軍慰安婦總計35名。”
“她們都風燭殘年了,身心俱疲。1/3以上的人不能生育,大多又家住農村,我要給她們養老送終。”
“我現在要拼命掙錢啊,”蘇智良笑了笑說道,“她們活著一天我援助一天。”就在前兩天,云南李連春老人的孫子高考分數出來了,考得不錯夠上本科了,可家境貧困,學費無法籌措。在云南打電話來報喜的時候,蘇智良還沒等對方開口提學費的事:“只要能上本科,費用我來,直到畢業。”
但僅憑一己之力又如何援助得過來?全國35名幸存的原日軍慰安婦,按每人每月100元的補助,一年需要4.2萬元,況且,“老人生了病怎么辦?甚至后代讀書沒有錢怎么辦?能坐視不理嗎?”
2000年,有一個“亞洲女性國民基金”找到蘇智良,表示愿意給錢援助老人。但接觸后,蘇智良發現這個組織是由日本政府和民間募捐共同出資,“目的是給了錢,就要我和受害的老人們閉嘴。”面對這種要求,蘇智良沒有考慮一秒鐘。
所幸的是,經過多次接觸,2001年“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”和蘇智良所在的上海師范大學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達成協議,部分出資幫助援助老人生活。“我現在想的問題是明年如何再提高老人的生活補貼,目前1個月100元太少了。” (新華網 )
|